|
陈建兴接受海都记者采访 6月11日讯(海峡都市报闽南版见习记者 陈莹钰 记者 谢明飞 文/图)在没有发生意外之前,陈建兴开着一家铸造厂,是个小老板,母校潘厝小学教学楼的募捐榜上,还刻着他的大名。可一夜之间,他的人生轨迹变了,因为故意伤害罪,他被判入狱3年6个月…… 陈建兴个头近一米八,是惠安东岭镇潘厝村人。昨天上午,53岁的他,开着越野车,经过家门前这条自己修建的村道,走进一栋三层楼白色洋房,云淡风轻地跟我们说起17年前,那场改变他和家人人生的意外之后,他曾经的不满和愤恨,释怀和拼搏。 高墙里,家人是最大的动力 1998年,陈建兴36岁。酒席之间,3个男子和他发生争执,面对围攻,他失手伤了人。直到被拘留,他才知道,其中一人的一只眼睛视网膜脱落,看不见了。 终审,他被判3年6个月,并要赔偿受害人1万多元。高墙里的生活,家人的探视,是他最大的动力。 “听家人说,在我羁押期间,我妈想尽一切方法来看我,可我已经被批捕,她没见着,哭晕过去。”陈建兴说,每次母亲来看他,都说自己身体好着呢,家里也很好,可是他知道并不是这样。 大儿子当时正要升初中,成绩不错,可以进提高班,但要多交50块钱。虽然年纪小,但他隐隐知道家里的变故,没说起钱和提高班。陈建兴至今仍觉遗憾和内疚,被自己养得好好的妻子,干农活、卖菜、打零工来补贴家用。铸造厂没了老板,突然倒了,借出的款项收不回来,反倒欠下10多万债务。 陈建兴说,服刑期间,两个念头支撑自己,一个是愤怒,他恨那些将自己害成这样的人;一个就是不甘心,“我从来没想过绝望,我常跟狱友说,像我们这样进来过的人,更要把自己看得重一点,如果你都把自己看轻了,还怎么指望别人看重你。” 2001年,他提前7个月获释,这是当时法律规定最大的减刑期。他说,就像不倒翁一样,一股力量压下去,是为了更高的弹起。 再从头,放下仇恨赚钱养家 陈建兴还记得,踏出泉州市监狱大门,是弟弟来接他的。一进家门,十多个亲人等着他,他有点蒙。 这座房,是他25岁那年盖的。他窝在卫生间里,水管露在外,生锈了,木门被白蚁蛀了,门锁松松垮垮的,他接了一桶水洗澡,凉水从头淋下,才一点点回过魂来。一切,都要从头再来了。 弟弟是包工做工程的,白天他帮忙做管理,负责分配、安排工人,一个月七八百块。晚上,他去开土方车,干点杂工。一天24小时,不管哪里有废铁,他就骑着摩托车去收。第二天一早,他将废铁分类好,拉去卖。 2004年,他做土方工程,赚了钱,慢慢开始买搅拌机、挂车、机械,还兼批发葡萄酒和代理净水器。2007年,他盖起这栋三层高的新房。 “有时会遇到当年那三个人,有的看到我就直接跑了。”陈建兴说,刚出来那阵,他也想过报复,但是这种念头总是一闪而过,“孩子这么多,我已经输过一次,再走歪路了,那一辈子就真的输了。” 带着对家人的责任,时间久了,仇恨慢慢释然。“说得粗一点,你撞到电线杆,难道还揍电线杆一顿不成,下次经过,绕开不就好了。” 看现在,捐资修路帮扶老人 这几年,四个儿女相继成家,家中添了5个孙子,两个儿子跟着他搞土方工程。 大儿子说,他和朋友都很佩服父亲,父亲好相处,工地的工人都愿意跟着父亲,最长的跟了18年。在工地里,父亲从来不会端着一个老板的架子,他亲自监工,谁干累了,体力不支,他就去帮忙。 提起陈建兴,潘厝村村支部苏书记也称赞,“很热心,村里修路,他捐了1万多块。” 原来,三年前,陈建兴家门前没有村道,只有一条田埂路。陈建兴和几个村民一起提议,把这条路修起来。陈建兴自己是修路的,便让村里赊账,先出材料和工人,填起这条4米多宽的村路。 “水泥路倒泥的第二天,我的小孙子出生了,村里老人都说,是我做好事才有好报。”陈建兴乐呵呵地笑着,一旁的朋友帮腔道,“他也捐资老人会。” “那也是小事,一次几千块,没什么好说的。”陈建兴赶紧说道。 现在的工地里,偶尔有老人来捡废铁,说要卖10块钱买菜,陈建兴都会让老人赶紧回家,工地危险,他拿10块钱给老人买菜。老人第二天再来,他也不烦,兜里便又少了10块钱。 快刀短评 对错 问题 从犯事到现在,都是17年,都是“事业有成”,但“逃亡”两字,改写了本该相似的人生。 惠安大叔陈建兴,入狱,减刑出狱,拼下了房子车子和事业,为村里修路,捐资老人会。村里的老人说,他做好事有好报。 安溪男子林某德,逃亡,隐姓埋名,组建新家,开了连锁药店,年入百万。他最怕天黑,每天都得借酒精让自己忘掉“我是谁”。 一个人犯了罪,人们说他是恶,他后来改好了,人们又说他是善,其实这不是善恶的问题而是对错的问题。陈建兴让人感念,是因为他在分清对错和善恶的基础上,帮了更多的人。 善恶有时候是一条路,指引人活得更好,可有时候又是牢笼,让人永远无法过得好。林某德的17年,艰辛地挣扎在这个牢笼里,即使家庭事业很成功,可没有酒精,他夜夜难眠。 做错了事接受惩罚,然后做对的事,不伤害别人,仅此而已。
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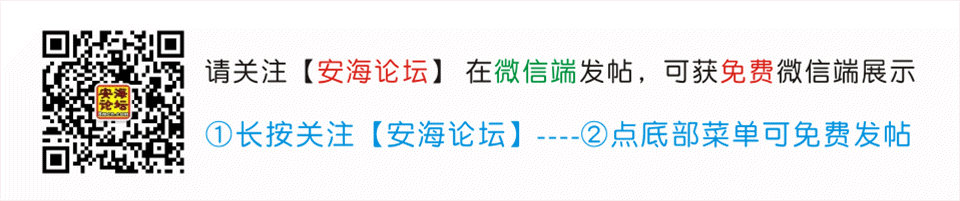
 /1
/1 
 |合作联系:13675910068|手机版|网站地图|小黑屋|安海论坛(www.8mcn.com)
( 闽ICP备09068224号-3 )
|合作联系:13675910068|手机版|网站地图|小黑屋|安海论坛(www.8mcn.com)
( 闽ICP备09068224号-3 )